长期以来,翻译文学被直接等同于外国文学,译者则是忠实复刻原著的文字搬运工,与创造性与想象力无涉。因此,翻译文学也就难入学者的法眼,成为文学研究的“弃儿”(谢天振语)。直到上个世纪末,在国内外学术潮流——包括海外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与内地译介学的兴起等——的驱动下,外国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以及中国近现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纷纷关注翻译文学,一时间热闹非凡。论者或是大开大合,借概论勾勒各时期翻译文学的发展轨迹,或是专注于个案研究,深耕细作地呈现丰富的翻译现象。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李今教授得风气之先,二十年前即开始关注此话题,《鲁滨孙变形记: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是其锱铢积累完成的第三部相关论著,串联从晚清到民国的重要汉译文学改写现象个案,兼具深度与广度。李著无论是理论运用,史料梳理抑或文本解读,对于翻译文学研究都贡献良多,具有典范性的意义。
正如副标题——“汉译文学改写现象研究”——所示,李著以“改写”(rewriting)作为统合全书的核心概念。这一术语自经美籍比利时裔翻译理论家及比较文学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在翻译研究领域早已深入人心。如今,海内外研究翻译的学者大多信奉“翻译即是改写”,也即是说,译者受到本土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的影响,会不可避免地对原著作出重新阐释。不过,勒菲弗尔对于“改写”的原初定义其实更为宽泛,包括所有为传播普及文学原创作品而展开的翻译、编史、选编、批评等行为。李今运用“改写”理论时回到勒菲弗尔的初始思路,因此全书得以涵盖三种类型改写现象:汉译文学中的改写(论述清末三种《鲁滨孙漂流记》汉译、林译“孝子孝女”系列小说、民初两种《简·爱》汉译)、外国作家形象的改写(包括高尔基、普希金)、汉译文学作品序跋中的改写(围绕“战争”、“革命”、“人”三种概念)。分别侧重译者对于小说文本的重新阐释,翻译及评论界对于外国作家形象的重新塑造,以及译作序跋对于核心观念的引介与重构。然而正如作者所强调的,全书主旨绝非以中国汉译文学个案来验证勒菲弗尔的理论,而是以“改写”概念为研究工具,借汉译文学的改写现象来“认知某一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与文学的独特光影,因而更偏向改写现象的历史研究”(第17页)。以第一章关于汉译鲁滨孙形象的讨论为例,李今在整体把握清末救亡图存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将三种译本与三位译者各自秉持的话语体系紧密勾连——沈祖芬译本体现维新话语,《大陆报》译本注入革命话语,而林纾译本更多地承载了儒学话语,从而生动再现了清末翻译小说所承担的功能与角色。与之类似,书中分析林纾翻译“孝子孝女”系列小说时,将其还原到五四时期“铲伦常”的舆论环境之中,展现出儒学信徒林纾借助翻译小说来扭转时论的努力。随后关于《简·爱》译本的分析充分结合民初通俗言情小说大盛的文化背景,对于高尔基、普希金形象流变的考察则放置在左翼文学的发展脉络之上。换言之,书中所论每一组汉译改写现象,都被作者紧密地编织在其酝酿产生与传播流通的历史语境之中,从而细致地呈现出翻译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双向互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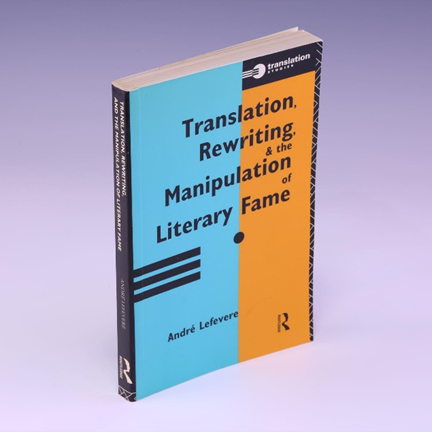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2017)
如前所述,以“改写”理论来审视翻译文学其实屡见不鲜,李著能够后出转精,与其对于一手史料的发掘和把握息息相关。由于学术积累不足,关于翻译小说的研究论文很容易陈陈相因,论者往往扎堆于晚清时段,反复分析的不过就是林译《黑奴吁天录》与苏曼殊译《惨世界》等有限的几部著作。李著的论题虽然同样从晚清起步,但是跨度甚广,涉及从戊戌变法到国共内战时期的多种翻译现象,且书中讨论几乎全部建基于一手材料之上。考虑到全书部分章节完成于本世纪初,其时清末民国期刊著作尚未电子化,我们不难推测作者为达成言而有据的论述,曾付出何种心力与劳力。譬如以往关于晚清《鲁滨孙漂流记》中译的基本情况,学界言人人殊,甚至题目与作者也张冠李戴,本书第一章以稳扎稳打的考辨提供定论,也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相对而言,林译小说大名鼎鼎,其来龙去脉早经马泰来等学者勾勒分明,但是学界中人往往只是从林纾的序言中寻章摘句来评价其译作,风行一时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孝女耐儿传》等林译小说几乎直到李今撰文才第一次得到详细的考察(在海外研究界,美国学者韩嵩文《林纾的文字制造厂: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成》一书可能最早析论《孝女耐儿传》)。周瘦鹃与伍光建在学界的热度不及林纾,但是前者的通俗小说与后者的翻译事业也早经陈建华、邹振环等学者阐发,不过两人的《简·爱》译本——《重光记》与《孤女飘零记》——依然有赖于李今首度析论。该章论述不仅厘清了《简·爱》的汉译史,也拓展了民国通俗小说研究的疆域。书中对高尔基、普希金形象的考察取材更为广泛多样,涉及译作、评论、传记、理论著作等多种类型,构成外国作家形象改写现象的完整资料链条。显而易见,作者具有敏锐的史料意识,这自然与其早先参与编纂《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初版本图鉴》的经验密不可分。延续一贯的思路,李今在撰写本书诸篇章的同时主编完成《汉译文学序跋集》(18卷),对清末民国的译作序跋作出通盘的梳理。正是以三千多篇文献为基础,方才能够完成本书第五章,考察“战争”、“革命”、“人”之观念的在现代中国的流变,取精用宏,论证严密。
在史料发掘之外,李著的文本解读同样精彩纷呈。对于专精现代文学研究的作者而言,文本细读乃是本色当行,以往关于海派小说的研究以及对鲁迅小说的细读皆是典型的例子。不过阐释译文与原创作品毕竟存在差异,作者主要以译作中的系统性改动及其驱动力为依据——这主要体现在以汉译小说改写为主题的前三章中——来确立阐释重点。套用勒菲弗尔的常用术语,书中所论译作之改写主要受到中国本土“诗学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牵引。就前者而言,最重要的诗学规范自然是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在《鲁滨孙漂流记》的汉译中,革命派知识分子完成的译本为教化大众而选用通俗的白话章回体,因此在塑造英雄人物主人公时受到《水浒传》人物刻画的影响,将原著中几近于患得患失的鲁滨孙转化成风风火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草莽英雄。周瘦鹃译《重光记》、伍光建译《孤女飘零记》实为清末以降言情小说潮流的产物,译者受此类小说传统牵引,强化恋爱情节,忽略原著小说的其他丰富意涵。与五四爱情小说相较,两作更为迎合读者趣味,凭借通俗的方式渲染奇情、真情,但并不逾越社会道德的规范。论述塑造改写现象的意识形态要素时,李著突出儒家思想扮演的至关重要角色。林纾以“业儒”自居,不仅以“中庸”来解释鲁滨孙的冒险经历,以“天”“道”解读鲁滨孙所崇奉的上帝,更为诸多小说中的外国人物行为模式赋予“孝”的道德动机,体现出融通中西文化信仰的努力,甚至是将儒学普世化的尝试。伍光建不若林纾一般对儒学心心念念,塑造简·爱时也征引《孟子》,将其视作“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女子人格典范。在小说之外,书中对于序跋等文类的解读同样细致,只是其识见更多体现在钩稽诸多文本背后的潜在关联上。以对“人”之观念的梳理为例,李著呈现出连续而又交错的历史演进过程:清末论者提及“人”时往往指涉族群与类型,五四时期周作人等知识分子开始取法欧洲战后思潮树立个人本位的人之观念,确立了“个人——人类”的阐释传统;三四十年代对苏联资源的译介和想象引进阶级话语,在冲击更新五四传统的同时又与之共存。

李今主编《汉译文学序跋集》(1894-1927)(第一至第四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虽然勒菲弗尔等理论家倡导的翻译学文化转向引发从“原著中心论”到“译著中心论”的转变,但是若要深入考察译文的改写,又不能不对原著作出透彻的理解。唯有在对读原著与译作之后,才能将“改写”的分析落到实处。就这一点而言,作者解读《鲁滨孙漂流记》《简·爱》等作品时所下的工夫不亚于外国文学研究者。对于此类英国文学名著,学界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流派纷纭,如何通盘把握阐释传统,又如何选取适切的阐释路径,在在考验研究者的眼力与能力。具体到《鲁滨孙漂流记》的解读,李著主要选择与后殖民主义对话,将鲁滨孙流落荒岛,大战蛮族,规训星期五等经历视作殖民主义话语试图宰制全球的产物。以此为参照,方才能够将沈祖芬、《大陆报》、林纾三种译本阐释为对于殖民主义话语不同方式的抵抗。李著对于《老古玩店》《简·爱》的阐释更注重叙述层次的辨析。前者的表层故事讲述耐儿与外祖父的流浪,借助其所见所闻与遭遇,批判现代工业文明;其深层结构则描述耐儿与外祖父逃离苦难,皈依天堂的朝圣之旅,以及回归田园的牧歌之途。无独有偶,《简·爱》看似一则世俗的恋爱故事,刻画出身低微的女主人公经历重重考验,与罗切斯特结成连理的经过。李今则结合以往的研究洞幽烛微,指出小说实则隐含着上帝之爱的故事,简·爱的人生历程也是天路历程。换言之,《简·爱》并非一般意义上现实主义的小说,而是处处充满基督教的隐喻。以上述解读为根基,李著精巧呈现出晚清民国译者林纾、周瘦鹃、伍光建对于基督教内涵有意的删改与无意的误读。因此,中国读者接受的其实是《孝女耐儿传》里小耐儿事大父奇孝的世俗伦理美谈,以及《重光记》《孤女飘零记》中孤女与落魄富豪的风花雪月故事。借助以上分析,李著提醒我们清末民国译者的改写其实构成了前述经典小说在中国语境里的阐释传统,后来的译者与研究者无不突出现实层面的主题,淡化甚至清除基督教内涵。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狄更斯长期被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简·爱》中基督徒圣约翰的形象常常被标签为伪善。除却整体解读原著思路,李著对于外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也颇为精准。譬如在研究左翼文坛对高尔基、普希金形象的刻画时,作者借助时人评论与后来研究指出,两位文学家地位在当时苏联文坛的浮沉也遥遥牵引了他们在中国的命运。
李今在导论中认为,汉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与原创文学平分秋色,精研汉译文学等于为现代文学研究再度开疆拓土。而鉴于翻译文学融合中西的特质,要适切地分析汉译文学,就不能不跨越学科的界限。虽然李今以现代文学研究者自居,认为相对于外国语言文学及比较文学者,自己更注重“考察译作的功能,特别是现代汉译文学如何回应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美学以及文化的各种需求而产生发展”(第7页),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作一种策略性的表述。——统观全书,无论外国文学研究的功底还是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皆清晰可见,只不过整合在现代文学研究的架构之内。换言之,《鲁滨孙变形记》生动地演示了如何跳脱学科的界限,在现代文学的视野中深入分析翻译文学。而书中稳扎稳打得出的研究结论与苦心经营创立的研究模式亦将为学界提供恒久的参照。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图片为作者提供)
本文原载“论文衡史”2023年1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