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国宝》:“青花束莲纹盘”与青花瓷的世界流行故事
新京报 编辑 何安安 罗东
作为国内吴文化研究与展示的特色文博机构,吴文化博物馆馆藏了一批吴地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如新石器时期的“黑衣陶刻符贯耳罐”、战国时期的“古琴”、西晋时期的“青瓷扁壶”、明代的“青花束莲纹盘”等。这些国宝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坐落于澹台湖景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及国保单位宝带桥南侧的吴文化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作为国内吴文化研究与展示的特色文博机构,这里馆藏了一批吴地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如新石器时期的“黑衣陶刻符贯耳罐”、春秋时期的“鹦鹉首拱形玉饰”和“楚途盉”、战国时期的“古琴”、西晋时期的“青瓷扁壶”、唐代的“双鸾瑞兽纹铜镜”、元代的“釉里红云龙瓷盖罐”和“朱碧山银槎”、明代的“青花束莲纹盘”等。
在《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一书中,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专家撰写十余篇专文,从吴文化博物馆馆藏的这些国宝级文物出发,在文物信息的基本阐释之外,融入当代艺术视角,以国宝文物及相关艺术内容的中西方比较、古今融合为逻辑,对文物进行再想象。
本文为其中《青花瓷与猫的世界性流行》一文,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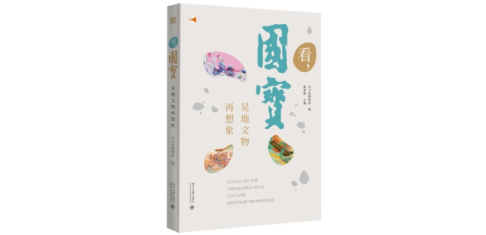
《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
编者:吴文化博物馆
主编:陈曾路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8月
西方人对瓷器的热爱
青花瓷、猫、世界,这三者能扯上关系吗?连接它们的,是自然。
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油画大师们已经能像人肉照相机那样在画布上再现地球上的万物了。正如今天的少年们学会了建模后不但能赚生活费,还总忍不住会在软件中捏出心中的女神。西方艺术家们也毫不吝啬地开始画出想象中的神仙和仙境。1514年,威尼斯画家乔瓦尼·贝利尼已是耄耋之年,竟然一反常态地画了一幅大型“异教”宴会场景。画面中的神仙都如古希腊雕塑那般隽永,表情也略显忧郁,反而凸显了画面上最亮眼的存在——三个青花瓷盆。

《诸神之宴》,乔瓦尼·贝利尼与提香,1514。《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瓷器的温润材质,让习惯了陶和金属的欧洲人欲罢不能。
西方人对瓷器的热爱一定很难被理解,毕竟对我们来说那只是饭碗而已,从小到大总砸碎过几只。这种热爱应该和以前旅游团打折季时去法国香榭丽舍大街抢购的盛况相仿。因为太过稀少,在文艺复兴时期油画上的瓷器,总是被放在神圣的场景之中。在曼特尼亚的《三王来朝》里,有一位来自东方的国王,脑门和头型很像寿星,手中端的瓷碗里盛满了黄金,而小小救世主似乎对其他两人的献礼不感兴趣,光盯着青花瓷看。
好奇心旺盛的艺术家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应该还买不起这种当国礼赠送的东方奢侈品,但只要他们在宫廷里见到过,总会想办法画到自己的作品中,或用手稿记录下这种奇妙的相遇。德国艺术家丢勒就在一张设计手稿中留下了几件瓷器,左边两件青花瓷显而易见,右边那个应该是被拉长的定窑白釉铺首耳瓶。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丢勒对三件瓷瓶都进行了挪用和改造:两个瓷瓶被加上了古希腊陶罐常见的把手,最精妙的还是把定窑瓷瓶左右两边的铺首放到了最下方的青花瓷上,不但改成了三个,还把从饕餮进化而来的铺首改成了狮子叼环。

丢勒手稿(左),大英博物馆藏,1515—1518;仿定窑白釉“云麓”款铺首耳瓶(右),明,故宫博物院藏。《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不愧是能对标达·芬奇的绘画大师,丢勒给我们上了一堂教科书般的文物再创作课,在一张手稿上就悄声无息地把瓷器优美的器形和纹案都学走了。那只来自印度的犀牛应该也没料到,它会因为丢勒的版画而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犀牛,虽然丢勒都没见过它,只是参照朋友信中的手稿和描述加点幻想就画成了。
聪明的艺术家模仿,伟大的艺术家偷窃。
这句话和丢勒都证明了艺术创作的基础就是临摹,不然考美术学院为何还要天天画大卫头像呢?
这张有瓷器的手稿仿佛画出了占有欲的几个阶段,从憧憬到拥有,然后就是改造和生产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古罗马开始,欧洲一强大,就会“拔”几根埃及法老的方尖碑插在自己的广场上,然后和丢勒一样,在古老的方尖碑上加些诸如十字架的自身文化元素,彰显对其完全的征服。这也不是什么怪事,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汽车或摩托车后,很多人不都打起改车的主意吗?哪怕年检时还要花钱改回原型。
文艺复兴之后的巴洛克时期
改造还不满足的话,就自己造吧。炼金术在文艺复兴时开始大流行,虽然“贤者之石”更像宗教传说,但破解中国瓷器的试验从未间断,万一成功的话可算是真正的“点土成金”了。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16世纪的炼金术士们在筹划了精密的生产工序后,打开窑的瞬间,看到了很多陶器。
纵然失败也不能放弃梦想,艺术家在马约里卡陶盘上巨细靡遗地画下了一位青年艺术家在画青花瓷盘的场景,陶盘上的艺术家一度被错认为是拉斐尔。但重要的是这幅陶盘画侧面证明了青花瓷能流行西方的原因——釉下彩。正是因为青花瓷上画有各种图案,酷爱形象的西方人才会欣然接受。在景德镇青花瓷风靡世界前,其实商道上流通着很多龙泉青瓷,但西方人可能比较难以直接理解这种几乎没有图案、特别“老庄”的东西。让那时的西方贵族在汝瓷和青花里二选一,估计选青花的要多很多。

马约里卡陶盘(左),约1510—1520;美第奇瓷器(右),约1575—1587。《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1575年前后,不光有钱还有艺术品位的美第奇家族开始烧制青花软质瓷,由于烧造时间只有十几年,现在存世只有60余件,稀有得像“西方的汝瓷”。相传“豪华者洛伦佐”就收藏了51件真正的瓷器,这些东方珍品还时不时被当成外交礼品送人。美第奇家族世代相传的艺术赞助经验和品位似乎让他们理解了青花瓷上的留白和图案本身一样重要,的确有几件美第奇瓷器称得上清雅。
但在其他赞助人和工匠的眼中,这些来自东方的植物图案,可能还是太扁平了,只有线条和单色的设计对他们来说真的少了些什么。在一本1557年前后讲述瓷器设计制作的书籍中,我们非常明确地看到了明青花上的花草纹案。但这种以线条为主的中式图案设计在书中只有一页半,剩下的设计图上的花花草草都开始有了厚重的体积感和阴影。
这种真实复写大自然万物的模式和图像,我们平时常常能在自然博物馆中看到。在青花瓷大量销往欧洲的同时,西方也开启了大航海和殖民时代,随船的艺术家在新大陆上,依然用人肉照相机一般的手法记录下无数奇珍异兽。当然,随后还有几声枪响,那些动物和植物就成了标本,标本和手稿被大量运回欧洲后也就慢慢形成了自然博物馆。这是西方近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总之就是占有。同时,中国的艺术家们依然追随着老庄,躺在山林之中。
文艺复兴之后的巴洛克时期,数以百万计的青花瓷销往欧洲,并且有更多的青花瓷在欧洲被制造出来。
在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流行达到顶峰
这种以前只有众神和国王使用的器皿也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欧洲正式开始吹起“中国风”。我们常常能不经意地在油画中找到它们的身影。
在荷兰的黄金年代,维米尔不但画下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惊鸿一瞥,也在接近毛坯的室内近景中画上放满水果的青花盆。可能怕画面过于四平八稳,维米尔还让瓷盆微微倾斜,有几个水果调皮地逃了出来,还有个桃子被切开后展现在观众面前。如果在中国看到一枝花开出墙外的图像,总会让人联想到那顶绿油油的帽子。外国专家也一口咬定画面中的女孩有了婚外情,在读情人寄来的书信,因为鲜艳欲滴的水果怎么想都不能象征贞洁。而且画面左边窗户大开,更别说用X光扫描这幅画时发现,白墙上以前其实挂了一幅丘比特。
不管这位妻子是否愿意在家做一块“望夫石”,但当时真的有很多荷兰老公在中国或新大陆做跨国生意,写下一本本带插图的中国游记回国发行,相当于出个差顺便把Vlog也拍了。总之,随着印刷术的流行和识字率的上升,这些与中国相关的书籍也助长了那时欧洲对中国的憧憬。
顺便一提,荷兰等新教国家不能有圣象崇拜,因而大教堂里巨大的宗教人像作品订单消失了。正因如此,画家们反而能把部分创意专注到器物上,因此留下了不少对瓷器的精彩描绘。到了今天,这些油画日积月累的龟裂,带给人一种瓷器开片的独特美感。
在这幅描绘中国商店的小画中,我们看到屏风、漆器和数不清的瓷器在勾起欧洲人的购买欲。商店的上方有很多东方绘画,但悬挂和观看方式依然是非常西方的。不管是彩色的细密画还是黑白的山水,都被装裱在画框之中。这种占有后改造的模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动植物标本、埃及方尖碑和丢勒的手稿中都看到过。

中国商店内景,1680—1700。《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我们也不会奇怪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充满了被金色金属镶嵌的瓷器。毕竟是太阳王嘛,照得整个凡尔赛宫都金灿灿的,宫中的瓷器也理所应当地要沐浴在华丽的金光之中。既然青花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连伦勃朗和维米尔这样的画家都买得起,那国王们只能更大鸣大放一点:欧洲各地都建起了瓷宫。凡尔赛宫以前还有从建筑外立面到内部都被瓷铺满的特里亚农瓷宫。
“蒙娜丽莎瓷砖,大卫拖把专家。”
家装相关广告好像只要和外国搭边就高大上了,在新中式和“侘寂风”流行之前,“简欧”统治了我们太久,神州遍地都是欧罗巴小区。而18世纪欧洲中国风的流行也到了顶峰,连家里瓷砖都是青花风格。
看看有些瓷宫,真的满到一个青花瓷盘都塞不进去了,而且这些瓷宫的主人也马上就要被各类革命或者拿破仑赶下台。接手中国风的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随着一届届世博会上日本馆的出现,欧洲上流社会开始吃寿司,凡·高开始临摹浮世绘作品,把自己头发剃光幻想当个日本僧侣。

德国夏洛滕堡宫瓷宫,1695—1699。《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瓷器是火与土的艺术
在画出《日出·印象》之前,莫奈为了逃避普法战争的兵役去了伦敦,有些学者认为莫奈的印象派画风受到了英国艺术家透纳的影响,毕竟透纳在印象派崛起的几十年前就画了好多雾蒙蒙的风景画。无论英法学者怎么抬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雾都伦敦的空气质量应该更差一点,印象派那看似江南烟雨的朦胧里肯定带着些有毒的颗粒物。工业革命破坏自然的报应快速地降临下来。自19世纪开始,在欧洲人涌向房价越来越高的城市的同时,城里人也开始乘着蒸汽火车逃离繁华,亲近自然。

青花束莲纹盘,明,吴文化博物馆藏。
如今的大都市中,人们离自然太远了。建筑里长棵草,都能变成网红打卡点。十二节气全靠朋友圈里的海报而知晓。有时出门下雨还想,老天爷的手机里没有天气预报App吗,不是显示阴天来着?
当代生活中,环顾室内空间,我们能接触到最接近大自然的存在是什么——是猫。它们冷不丁地纵身一跃与时不时伸出的利爪都在彰显自己在野外的生存能力。人类忙了几千年也没有驾驭这小小的野兽,还老是被猫驯服,称其为“主子”。有时,猫身上那种自由自在的随机性,就像强大的自然现象,也像一件无法被装裱束缚的当代艺术品。不管李诞会去救猫还是救《蒙娜丽莎》,但对猫来说,《蒙娜丽莎》可能也就是块木板。
在艺术家施皓敏对青花瓷的再创作中,瓷盘上的花草图案已开始生长蔓延,一个青花瓷盘可以改变整个空间的气氛。自古以来,西方艺术把人体视为至高的主题,用大理石塑出古希腊运动员完美的六块腹肌,而中国艺术崇尚自然,瓷器本身就是火与土的艺术。源自大地的瓷土借水成坯,在依山傍水的龙窑中,火焰赋予其生命。吴文化博物馆所藏的青花束莲纹盘更是全部被植物纹样所覆盖,平静的表面下涌动着大自然的能量。细看上面的青色,有细腻的晕染层次,瓷器烧造的过程本来就有一定的随机性。在艺术家的再创作中,我们也能看到微妙的颜色变化,画面中时不时染出些紫色和绿色。

青花喵,施皓敏。《看,国宝:吴地文物再想象》插图
在万物互联、数据量化、算法主导的时代,可能我们更需要猫来慰藉,哪怕是突然被猫咬了一口。它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与傲娇态度,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也快速占领了短视频网站的推荐位。
当然,猫和青花瓷都是让我们在室内遥想自然的媒介,最重要的还是出去走走。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引入中国后,选的是景德镇的浮梁和南海,也有更多的本土大地艺术节在路上。宗旨很简单:“选离城市最远的地儿,做最艺术的事儿。”自然能治愈我们,也需要我们的治愈。
原文作者/罗依尔
摘编/何也
编辑/罗东
导语校对/柳宝庆
